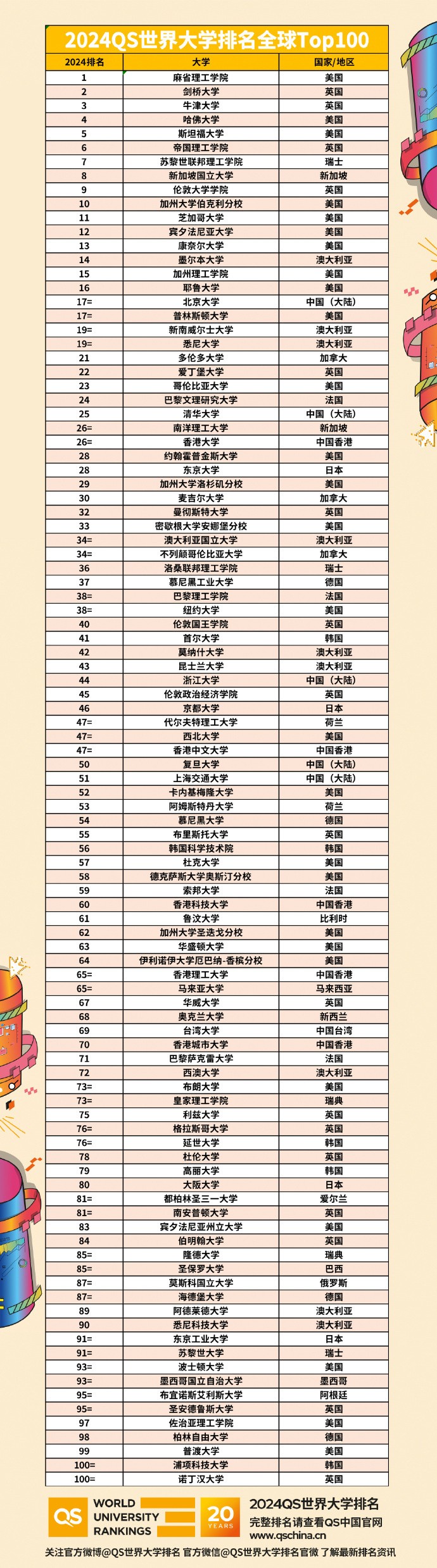香港新聞網10月6日電 202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。挪威劇作家約恩·福瑟獲獎。在當代歐美戲劇家中,他的作品被搬演的次數最多。 這位64歲的挪威劇作家,作品已被譯成四十多種語言,製作成九百多部舞台劇,在世界各地上演。因為在戲劇領域的傑出成就,他得過包括易蔔生國際戲劇獎、斯堪的納維亞作家獎在內的諸多獎項。《紐約時報》評價,他的作品“充滿激烈的、詩意的簡潔”。

易蔔生國際戲劇獎給他的授獎詞稱:“福瑟迫使劇場和它的觀眾們以全新的方式思考。他是未知的詩人。” 孤獨、愛和死亡,是福瑟一直探討的主題。
2014年,他的戲劇選集《有人將至》在中國出版。2016年夏,他的第二部戲劇選集《秋之夢》在中國出版。他也曾來到中國,觀看上海戲劇學院演出自己的名作《有人將至》。他認為,這個版本是對自己作品最好的舞台呈現之一。
2016年9月26日,騰訊文化頻道電話采訪了在奧地利的福瑟。如今,我們重溫这篇訪談內容(編者注:原文引自騰訊文化頻道公眾號),或許更能瞭解福瑟和他的作品。
寫劇本就像在編曲
問:“大海”在你的作品中分量很重,往往奠定了全文基調。它有時給人安全感,更多時候卻令人恐懼。為何這樣描寫海洋?你的主人公經常長久地凝視大海,你也會這樣做嗎?
福瑟:是的。我在挪威卑爾根附近的小鎮豪格鬆德長大,在那里總能看到海和海浪。這對我影響很深。坐下來集中精力寫作時,我的腦海里總會浮現出自己第一次看到海、看到船的情景。 現在,我有時也去卑爾根附近的一所房子寫作。它離海很近,從那里二樓的書房眺望,可以看到海、海浪和峽灣對面的陸地。我經常會在那里凝視大海。我在挪威北部山區,我還有一座小木屋。那里更開闊,可以看到更大的一片海。 我父親喜歡船。他有一條船。後來,我也有了船。我現在用的是一條鄰居造的小木船,天氣好的時候,我會沿海岸線駕駛它。在廣闊的海面上,你會感覺到自由。但同時,這種自由是有限的——所有的時間里,你都必須呆在船上。你會熱愛大海,會喜歡海浪的節奏、海水變化的顔色,但同時你也會發現大海的危險:它變化無常,發怒時會很殘酷,很多人葬身其中。我想,大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地,仿佛意味著死亡。 可以說,大海是個矛盾體。我的作品也是個矛盾體。而這是因為,人生本身就充滿了矛盾。
問:你反複書寫人的孤獨感:“我將只有獨自一人。”這與你的成長經歷有關嗎?
福瑟: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,我的孤獨感要追溯到我的嬰兒時期——它在我一兩歲時就出現了。從小到大,雖然有很多親密的朋友,但我一直性格內向,有些害羞。我感到我和他人、和整個世界的距離都很遠。正是為了減少這個距離,我開始寫作。
問:你最早寫的是短詩和歌詞。當時的你是怎樣開始創作的?這段經歷對你的戲劇創作有什麼影響?
福瑟:12歲時,我很喜歡彈吉他,就開始編一些小麴子,也為它們寫歌詞——我至今依然記得其中的幾首。16歲時,我參加了一個樂團,彈搖滾吉他,也拉小提琴。但我最終意識到自己沒多少表演天賦,就放棄了演出,繼續編曲。 可以說,我的寫作就是從與音樂有關的創作開始的——音樂需要聆聽,寫作也需要。有時我感覺自己只是在聽我的人物說話,然後把它們記錄下來。 我的作品“語句重複”的特點,也是從那時開始的。寫劇本時,我就像在編曲,戲劇就仿佛是我的樂譜。
問:你曾如此熱愛音樂,那你最喜歡的音樂家是誰?
福瑟:約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。沒有音樂家能和他相提并論。
問:寫作之初,哪位作家對你的影響比較大?
福瑟:最初開始寫作時,挪威作家羅爾夫·雅各布森對我的影響很大。當時我的作品仿佛都不是用自己的語言寫成的,而是用他的語言寫成的。直到二十多歲時,我才逐漸形成自己的語言。我正兒八經在報紙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叫《他》。我後來的作品風格,和那篇故事的差不多。寫的是生活的本質,與人物的名字無關。
問:一開始,你發表的是小說。十多年後,你的劇作《有人將至》才真正問世。你是如何從小說轉向戲劇創作的?
福瑟:說實話,我的第一部戲完全是別人掏錢聘我寫的:有人問我想不想寫戲,那時我是自由作者,收入不高,非常需要錢,就接受了。在此之前,我從未想過會寫戲劇。 用了一周時間,我寫了《有人將至》。在我的作品中,它至今仍是被搬上舞台次數最多的一部。 我并不喜歡劇院,甚至有點討厭它,但我喜歡寫戲劇的感受——不僅可以決定如何使用語言,也可以決定在何時沉默。沉默是語言之間的間隔。
問:說到這一點,你的戲劇的一大特點,就是靜場的頻繁出現。在你看來,沉默在戲劇中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?你如何判斷哪里該沉默?
福瑟:沉默和孤獨有關。這種孤獨并非是一種壞事,而是一種平和。沉默也和虛無有關,而沉默和虛無都是我作品的血肉。我認為這些停頓或者沉默,比那些說出來的話要有分量得多。這種沉默也會令觀眾感受到氛圍的緊張、故事的戲劇化。 在寫作的過程中,我很容易意識到哪些地方需要短暫的停頓,哪些地方需要長久的沉默。
問:家庭關係是你關注的另一主題。在這方面,你本人的經歷是否影響了你的創作?(注:福瑟離過兩次婚。)
福瑟:在我的作品中,所有情節都與人物之間的關係,或與他們因為缺少某種關係而導致的虛無感和空虛感有關。其實在人生中也是這樣。我自己關於各種關係的感受,影響著我的作品。 不過,所有的好作品都要包含人生,也要和它保持一段距離。
問:在你的劇本中,人物多為無名氏,人物名往往只是“一個人”“另一個人”“他”“她”。為什麼這樣設計?
福瑟:一開始寫作時,我就沒給主人公起正式的名字,只用“他”或“一個男人”來指代。然後我就習慣了這樣做。我或者不用具體的名字,或者一遍遍地用同樣的名字指代不同角色。 名字本身會透露太多信息,產生太多干擾——一個女孩的名字可能暗示了她屬於某個社會階層,來自哪個國家。這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寫的是生活的本質,和人物的名字無關。

約恩·福瑟 資料圖
故意反叛貝克特,未受易蔔生影響
問:在你的早期作品中,有的是以時間順序來安排的,比如《有人將至》就分開始、中場和結束。但在你的後期作品中,過去和現在混合、滲透在一起。這在《秋之夢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。你在後期為何這樣處理?
福瑟:我將過去和現在的混合與滲透稱為“片刻”。比如我的戲劇《睡覺》,就是發生在某一片刻的故事。片刻和永恒是聯繫在一起的,它描述的是一種狀態。它看似不存在,但實際上又存在。 在作品中,假如將某個片刻獨立出來并加以擴展,我想,這部戲就不再像是一曲音樂,而像是一幅畫了。
問:請談談影響你的戲劇和劇作家。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對《有人將至》的創作有怎樣的啟發?
福瑟:年輕時,貝克特的作品非常吸引我,我也很崇拜他。他給了我很多啟發,但在某種程度上,我故意反叛貝克特——我故意寫得和他不一樣。所以我的《有人將至》實際上和《等待戈多》是相對的。在《等待戈多》中,他們等啊等,沒有人來;但在我的戲中,他們不用再等了——有人來了。 當然,我的性格和貝克特的不同,我們的作品風格也不相同。我并不認為我的作品受貝克特的影響。
問:那易蔔生呢?
福瑟:易蔔生從未對我有多大的吸引力。我反而對那些挑戰易蔔生戲劇的作品很感興趣,比如貝克特的——它們和易蔔生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截然相反。 易蔔生與莎士比亞、契呵夫一起被譽為世界三大劇作家,但我從未覺得和他很親近,也從未覺得他影響過我的寫作。我和易蔔生的區別很大。
問:據你觀察,在你創作戲劇的這些年里,歐洲的戲劇創作有什麼明顯的變化趨勢?劇作家的生存狀況如何?
福瑟:在歐洲,戲劇最繁榮的國家是德國,這種繁榮也擴展到意大利、法國和挪威等地。我覺得歐洲各國的戲劇發展狀況都差不多。一開始,歐洲的劇院非常熱衷於將原創的新劇本搬上舞台。但是後來,越來越多的劇院導演開始決定戲劇的內容。他們傾向於將小說改編成劇本,純粹的原創劇本不再受重視。我并不喜歡這樣——大多數劇院導演并非天才,排的大多數作品不值一看。 在歐洲,當劇作家的收入并不豐厚。和排新戲相比,導演更愛將經典戲劇再次搬上舞台,觀眾對新戲的興趣也不大,所以被搬上舞台的新戲很少。這是我自己的感受。
“希望中國讀者看到我的更多戲劇”

約恩·福瑟作品《有人將至》中國版劇照 圖源:騰訊文化
問:《有人將至》曾被上海戲劇學院搬上了中國舞台。你也來中國看了這場演出,感受如何?
福瑟:印象非常深刻!我看過很多場根據《有人將至》編排的舞台劇,中國的這場如果不是最好的,也是最好的之一。在演員的表演、場景的佈置和裝飾及聲音的處理等方面,它都很好。比如舞台上的流水聲并非是提前錄的,而是工作人員現場製作的。我認為,這場演出非常準確地理解和再現了我作品中的音樂和情緒。 演繹我的戲劇,不光靠對話,還要靠很多沉默的時刻,以及人物的肢體語言和表情,比如手勢的一個小小的變化。這場演出對此也把握到位。這些都是我喜歡的。
問:你說,東方人仿佛能比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你的作品。這是為什麼?
福瑟:我也無法解釋,上帝才知道。我的戲劇在法國也很受歡迎,但我發現,最能演繹好我的作品的,是東方的演員;最能理解我的作品的,是東方的觀眾。 我的中譯者鄒魯路是當代歐美戲劇研究學者,她正在探尋我的寫作方式與亞洲人心理之間的關係。最近她告訴我,上海戲劇學院打算在中國出版我的另外兩部作品,對此我很開心。希望中國讀者看到我的更多戲劇。
問:你在2014年錶示不打算繼續寫戲劇了。那你最近在創作什麼?
福瑟:我已經寫了三十多部戲,包括二十多部長戲和十多部短戲,我覺得寫够了。戲劇需要一定的舞台性和緊張情緒,但這種緊張情緒太多了,我感到疲憊。我現在需要安寧。 我最近一直在寫小說、詩歌和散文,這也是我最初的愛好。去年,我的小說三部曲《不眠之夜》《奧拉夫的夢想》和《倦怠》贏得了北歐理事會文學獎,這是北歐最高文學獎。
我一直想寫“慢散文” (slow prose)。現在我就在挑戰自己,寫一個這樣的長篇。我已經寫了1500頁。它將分三卷、七部分,在2019年、2021年和2023年出版。(編者注:福瑟說的這三部慢散文成為他的代表作,也是今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力作。他在2019年至2021年分三卷出版了三部曲,書名分別是《另一個名字》、《我是另一個》和《一個新名字》。三部曲合稱《七宗論》。這三部曲講述的是一位年老的畫家和鰥夫孤獨的生活,他在連續七天的生活中需要面對以及思考宗教、身份認同、藝術以及家庭生活的現實問題。) (完)